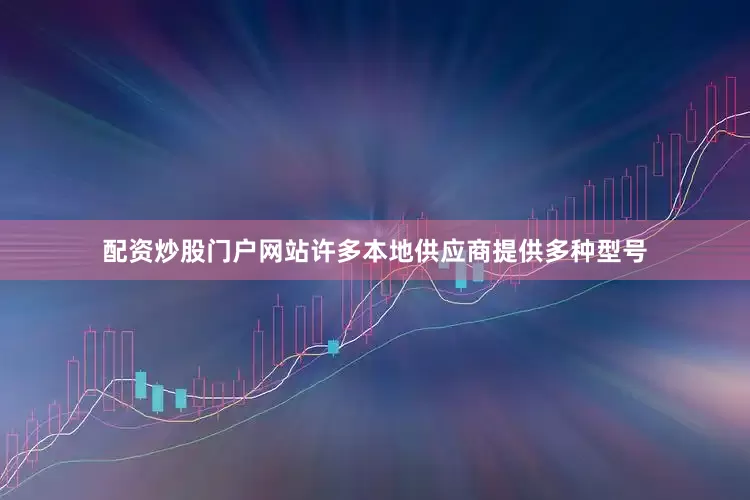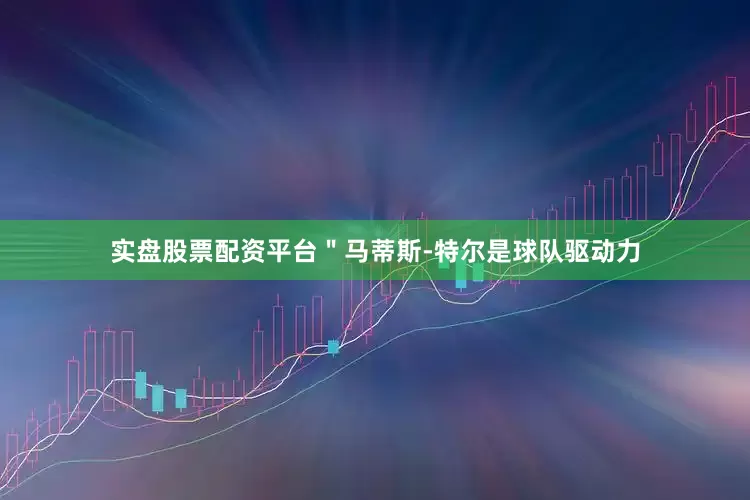街角面馆的玻璃总蒙着层油雾,一次性筷子掰开时总挂着几根毛刺,听见对面塑料凳"吱呀"响了一声。她裹着褪色的牛仔外套坐下,袖口似乎还沾着颜料——那副画是春天画的,具体什么颜色记不清了。
"昨天那通电话是骗人的吧?"她说话时在搓外卖袋的提手,哗啦哗啦响得像是要拆开什么。蒸笼腾起的热气扑在她睫毛上,凝成细小的水珠。我站起来时,她转身了,我没开口,她没回头。
成年人的谎言都沾着烟火味。她说要穿新衣服给我看时,隔壁桌大爷正吸溜着面条。我盯着他碗里晃动的油花,想起那年冬至她非要煮的芝麻汤圆,粘在锅底上的黑芝麻糊是真难洗啊。
"没骗人。"这话说得像菜市场尾摊蔫掉的芹菜。
疫情那年囤的酒精喷瓶还在玄关挂着,瓶身贴着便利贴早褪成淡黄色。她说"放我走"时,收银台正好响起"到账15元",突然让我想起漏在聊天记录里的半截情话,好像多年的过往和守候顷刻间将化为乌有。
"还是希望你过得好。"这句话飘进后厨油锅的滋啦声里。老板娘端来两碗葱油拌面,我们谁都没动筷子,任由面条坨成了冷掉的棉线。
展开剩余49%我们没说分手,就像还留着对方的外卖地址般。在衣柜最底下发现她忘拿走的绒睡裤时,鬼知道我是想把衣服还给她,还是想见她,犹豫好久后,那通电话终究是没拨出去。
每当情绪找不到出口时,我喜欢去健身房撸铁。她突然打来电话,说要给我看新衣服。以前总笑她买的T恤洗两次就起球,现在阳台上晾着的衣裳,袖口早磨出了毛边。
"等见面穿给你看啊。"这话像是有人往喉咙里灌了瓶醋,酸味混着汗腥气直冲鼻腔。我看着汗珠子在哑铃上缓缓洇开,始终想不明白隔了这么久,这通电话的意图到底是什么,可当时就觉得空落落的心里又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最后一次见面,是凌晨十二点多。她下楼接我时,本想着会有个久违的拥抱,哪曾想见到彼此的瞬间,距离感仿佛已经提前丈量好了距离。她以前总说我敏感,我不以为意,可那天我真的敏感到抓狂,我想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,找到别人来过的痕迹。
我内心平静,行为却莽撞,比如当我拿起她的手机时,她说,“如果你敢看我的手机,我们将再没有以后。”当然,最后我放下了手机,不是害怕我们再也没有以后,是真害怕看到其他不该看到的。
后来离开时,拒绝了她的相送。走到那条水泥路尽头,撞见位卖栀子花的老奶奶,竹篮里有朵白花,颤巍巍地像是口袋里被手汗浸湿的珍珠耳环。买下那朵白花时,偷偷将耳环放在了竹篮里,我很想扔掉它,但又真心希望她过得好。
发布于:江苏省灵菲配资-正规杠杆炒股平台-配资知识网站-股票配资网站有哪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没有了
- 下一篇:中国股票配资网在线登录命令继续在朝鲜坚持抵抗